2022年4月1日上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研究》系列讲座的第三讲在考古楼A座101教室举行,本院丁雨老师为主讲人,讲座题目为“斯瓦希里考古研究史——兼谈东非出土的中国陶瓷”。讲座的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斯瓦希里考古研究史概述,二是当前斯瓦希里考古中的中国陶瓷研究。

图 1 丁雨老师
一、斯瓦希里研究史概述
丁雨老师指出,英文中的Swahili(中文音译为斯瓦希里,下同),根植于阿拉伯语中的“Sahil”, 有边缘或海岸之意,在阿拉伯地理中也常有“贸易港口”之意。斯瓦希里地区今常用来指代非洲东部大致从索马里摩加迪沙(Mogadishu)到莫桑比克赤布尼(Chibuene)一线绵延约两千英里的沿海地带,其包括了非洲大陆东部边缘地区和众多离岸岛屿。从地理位置来看,这一地区处于非洲大陆与印度洋的交界地带,自古便是各类人群的接壤之地。不同背景的人群在海岸地带交流、碰撞、融合,由此逐渐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海岸人群和相应的文化,即斯瓦希里人与斯瓦希里文化。斯瓦希里地区是印度洋贸易圈和非洲贸易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1498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之前,这一地区的情况鲜见于各类文献。因此对这一地区1498年之前历史的研究,主要仰赖于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探索。

图 2 东非沿海地区的主要聚落
斯瓦希里考古一般以斯瓦希里人所创造的诸多文化遗存为主要研究对象。从1948年英国学者柯克曼(J.S.Kirkman)发掘格迪(Gedi)遗址算起,围绕斯瓦希里人群及其文化开展的考古工作与研究已有70多年的历史,相关成果十分丰硕。不过,由于斯瓦希里考古工作与研究主要由欧美学者和非洲学者进行,东亚学者参与相对较少,因此,相关研究成果和研究进展在东亚地区的刊布也相对较少。然而,从宏观空间来看,东亚与东非地区位于海上丝路的东西两端,两地人群都是印度洋贸易的重要参与者,彼此之间互为重要的供货商和消费者。了解、探索斯瓦希里地区的历史,对研究古代印度洋的贸易情况和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实质地位颇有必要。
斯瓦希里地区的考古工作可分成三个阶段:
(一)斯瓦希里考古产生的背景与萌芽(1948年以前)
(二)斯瓦希里考古研究的早期阶段(1948-1980s)
(三)斯瓦希里考古研究取向之争(1980s至今)
(一)斯瓦希里考古产生的背景与萌芽(1948年以前)
1498年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后,东非沿海地区进入欧洲人的视野。达·伽马等欧洲航海者记录了在东非地区的见闻,其中零星记录了斯瓦希里地区相关的口述传说与历史。这些记录产生于现代人类学、考古学出现之前,虽是航海活动的副产品,但却对研究早期历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也可被欧洲各类考察活动的先声。
此后随着欧洲势力的渗透,前往非洲的欧洲人数量不断增多,欧洲人对非洲的记录在数量上大大增加,甚至堪称“浩如烟海”。不过,一方面,在1880年之前,欧洲诸国对非洲的掌控有限,只有少数地点处在欧洲国家的直接统治之下,非洲大陆有80%的地盘仍由本土人控制,这一情况影响了相关记录的广度;另一方面,众多欧洲记录者的身份复杂,包括了传教士、商人、旅行家、移民等等,其水平参差不齐,记录重点亦有差别,这则影响了此类记录的深度。
在众多记录者中,地理探险家是探索非洲地理和地表遗存的先锋,其在非洲的活动于19世纪中叶及其以后渐入高潮,涌现出如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史丹利(Sir Henry Morton Stanley)、伯顿(Sir Richard Francis Burton)等一系列卓有成就的人物。这些探险者除对非洲自然地理颇有兴趣外,也对非洲地区的人类遗存有所记录。在这一过程中,东非斯瓦希里地区的众多大型遗址获得了相应的关注。伯顿的著作《Zanzibar: City, Island and Coast》出版时,他已经声名在外,其影响力使得他对东非沿海遗存的看法广为传播,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图 3 Sir Richard F. Burton
以地理探险家为代表的众多先驱对非洲地区的深入探索,客观上加深了殖民者对非洲地区的了解,为瓜分非洲奠定了知识基础。1884年,欧美列强于柏林会议瓜分非洲。根据这次会议,东非地区主要由英国、德国、葡萄牙、意大利、法国五个国家占领,这些国家分别掌控大体相当于今肯尼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索马里、马达加斯加的区域。在斯瓦希里地区的核心地带——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沿海地区,角逐的主角是英国和德国。柏林会议后,两国继续在东非扩张,于1890年完成对这一地区的瓜分,英国占领了肯尼亚、乌干达和桑给巴尔等地,德国则控制了坦噶尼喀、卢旺达和布隆迪。不过德国在东非地区的殖民相当短暂,一战战败之后,坦噶尼喀由英国委任统治。由此斯瓦希里地区的中心地带基本为英国所掌控。得殖民之便,一些英国人展开了对斯瓦希里地区聚落更深入的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其历史更系统的撰写。斯蒂甘德(C.H.Stigand)、皮尔斯(F.B.Pearce)、因格拉姆斯(W.H. Ingrams)、格雷(Sir John Gray)等人的著述是这一时期此类探索的代表。
这四位作者均曾服务于英国驻东非的政府部门或军队,受教育程度较高。斯蒂甘德是一位军人,其于1913年出版《The Land of Zinj》,此书包含的诸多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材料,对多个学科均具参考价值。皮尔斯少校(Major Pearce)著述的《Zanzibar: the Island Metropolis of East Africa》首次系统介绍了隐藏于桑给巴尔和奔巴丛林中的波斯人、阿拉伯人的遗址废墟,引发了人们对这些遗存的关注。因格拉姆斯1919-1927年任职于桑给巴尔,其著述的原始资料基本来源于他在当地的收集,这也是其工作在多年后仍然受到称许的重要原因。约翰·格雷爵士是这一时期此类研究的集大成者。时人评价格雷的工作:“他更像一个古物学家而非历史学家”,这一论述虽然意在批评格雷的著述缺少对历史事实的讨论,却也透露出格雷选取材料和叙史的倾向。或许正因如此,格雷的工作颇受后来的考古学者和人类学家好评,认为他是一位专业的而非业余的历史学者,甚至认为他的著述能够取代前述诸人的成果。

图 4 Sir John M. Gray
在欧洲列强殖民东非的背景之下,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对斯瓦希里地区历史的探索主要由欧洲人进行。这一背景也决定了后来斯瓦希里考古工作及研究的开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由欧美学者为主导。在专业考古学者进入斯瓦希里研究领域之前,早期探索者虽然有相当部分并未接受过专业的文史学科训练,但往往接受过良好教育,其知识水平和个人素质在社会中相对较高,因此有能力完成具有一定水准的著作。同时,这些著作往往立足于作者本人的实践经历,他们的所闻所见后来未必能够全然保留下来为后人所知,就此而言,这些记录中的某些部分具备一手资料的价值。这些工作为此后斯瓦希里考古工作和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考古学、人类学、现代语言学等能够研究缺少文献地区历史的重要学科,几乎都是在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逐渐成熟并产生影响的。从伯顿(1872)到格雷(1962)著作结构、内容安排的变化,可以明显观察到这些学科影响力的逐步彰显。这一背景对斯瓦希里考古工作的出现具有促动作用。不过,在真正的考古工作开始之前,众多遗存对书写斯瓦希里地区历史的作用终究有限。
(二)斯瓦希里考古研究的早期阶段(1948-1980s)
1948年,柯克曼被任命为格迪(Gedi)国家公园的负责人,开始了对格迪遗址的正式考古发掘。此项持续11年的发掘,是首次围绕斯瓦希里文化遗存开展的专业考古发掘工作,其揭开了斯瓦希里考古的序幕。
对于柯克曼本人来说,东非的这份工作也为他带来了终身志业。柯克曼出生于1906年。他毕业于剑桥大学,曾于1934年在莫蒂默·惠勒爵士的指导下参加过梅登堡(Maiden Castle)的发掘,之后又在詹姆斯·斯塔基的领导下参与过中东《圣经》中的城市拉吉的发掘。从格迪遗址开始,柯克曼先后主持发掘了众多东非沿海遗址,其足迹遍布英属东非(大体相当于后来的肯尼亚、坦桑尼亚两国范围)沿海地区的重要聚落。在考古调查与发掘的基础之上,柯克曼发表了众多考古报告和研究著述,其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初步建立了系统的斯瓦希里考古体系,为斯瓦希里考古研究的开创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斯瓦希里考古的先行者,柯克曼的工作方法无疑对后人有重要参考意义。其撰写报告的体例和方法为奇蒂克等人所继承和发展,基尔瓦、曼达等重要遗址考古报告的写作均基本沿袭了格迪报告的结构安排,这实际也显露出柯克曼工作方法的影响。

图 5 J.S.Kirkman
考古学自诞生以来便是“混血儿”——它虽立足于田野调查和发掘,但其实施和研究过程,却需要多种资源和多学科研究的支持。有些学者虽非纯粹的考古学者,但在其他方面为推动斯瓦希里考古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弗里曼·格伦威尔(Greville Freeman-Grenville)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虽然弗里曼的研究主要依赖于文献资料,但其在撰写《坦噶尼喀海岸的中世纪史》时关注到出土钱币对于研究当地年代的价值,同时其在论述中注重利用已有的考古、文物材料,并在书后列出了坦噶尼喀沿岸众多历史遗址。弗里曼在利用考古材料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文献的价值。他汇编的《The East African Coast-select documents from the first to the earlier nineteenth century》是研究东非海岸历史的必备工具书。此外,弗里曼还推动了英国东非研究所(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 Africa,简称BIEA)的成立。这一机构为斯瓦希里考古工作提供了很多资源和支持,是今天支持和进行东非考古研究的最重要机构之一。
英国东非研究所成立之后,在斯瓦希里考古方面成就卓著。在这一过程中,其首任所长奇蒂克(H. Neville Chittick)主持了一系列斯瓦希里海岸最重要遗址地点的发掘。其主持的最著名工作莫过于1961年马菲亚岛(Mafia Island)相关遗址、1958-1865年基尔瓦遗址、1965-1978年曼达遗址的保护和发掘,其中又以后两者最为人所瞩目。
基尔瓦是斯瓦希里地区最重要的遗址之一。它曾控制东南非地区的黄金出口,是13-14世纪斯瓦希里地区最为兴盛的聚落,深入参与了古代印度洋贸易。奇蒂克主持的发掘工作,以基尔瓦岛东北角的基尔瓦城为中心。据奇蒂克估算,基尔瓦城遗址占地面积约一平方公里。这一占地规模在目前所见的斯瓦希里遗址中居首位。因此奇蒂克并未采用全面揭露的方法,而是在城内城外的重点地区分散布置发掘区域.从发掘方法来看,由于基尔瓦城遗迹集中地区,地表往往留存有众多石墙遗存,因此奇蒂克的发掘方法较为灵活。原则上,他遵守探方法,采用5x5米的探方发掘,但在不同的地表条件下也多有变通。与柯克曼相比,奇蒂克更加注重地层情况的披露,几乎每处布方区域,均配有详尽的地层剖面图。这一做法,似乎是受到了惠勒的影响。惠勒强调探方法,强调隔梁剖面的重要作用,因为通过剖面能够看到遗址的垂直序列,有利于遗址的分期研究。或许正因如此,在奇蒂克的报告安排中,紧跟其后的便是各个发掘区域的分期分析。
基尔瓦之后,奇蒂克又在另一处重要遗址曼达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基尔瓦是12-13世纪崛起重要城镇,曼达则是兴盛于9-10世纪的贸易中心。从曼达的考古报告来看,奇蒂克在曼达延续并巩固了他在基尔瓦的工作方法,同时也有一些进步。比如在基尔瓦的报告中,除珠子等遗物外,缺少其他遗物的统计数据,在曼达报告中则加入了对陶瓷、玻璃等一些遗物的统计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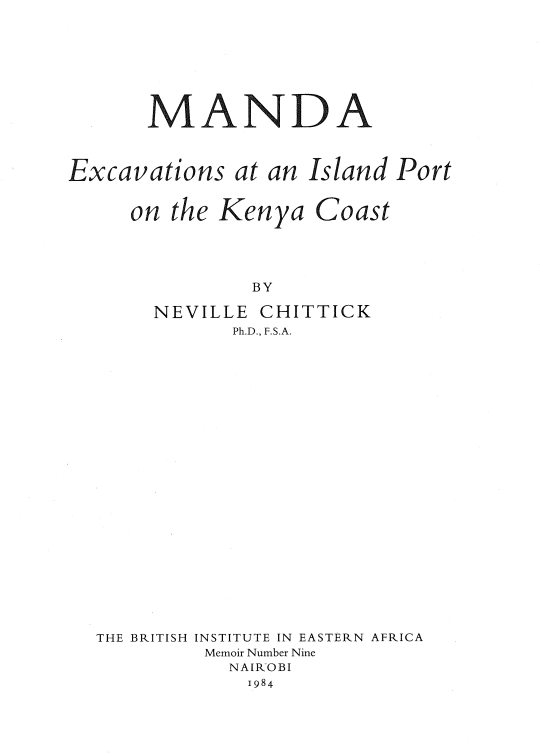
图 6 曼达遗址发掘报告扉页
柯克曼、弗里曼、奇蒂克等人对斯瓦希里地区遗存及历史的研究,具有开拓性,且具有示范意义。众多资料的披露,使得学界有机会重新审视当地文明的形成、发展,及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不过,囿于条件,其资料刊布方式亦存在明显缺陷,比如彩图过少、统计数据相对较少,不利于后人根据其成果进行再研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更多不同背景学者的加入,早期学者的研究取向也遭遇了挑战。
(三)斯瓦希里考古研究取向之争(1980s至今)
从19世纪中后期探险者关注到东非独特的废墟遗址起,人们就开始思考创造这些宏伟石质建筑背后人群和文明的起源问题。早期的探险者和“业余”学者都关注到了东非沿海地区的众多遗存与中东地区阿拉伯人、波斯人的关联,有些学者甚至明确提出斯瓦希里人是阿拉伯人、波斯人的后裔,或是阿拉伯人、波斯人与当地人结合的子孙。此类观点的提出者,未必带有主观恶意,但是由于提出者以及提出观点的时间节点,都处于殖民背景之下,因此不可避免地会让人将古今情境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客观来讲,斯瓦希里地区石质建筑、外来陶瓷、外来钱币等遗存,确实也更容易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所以,这一境况和由此产生的观点倾向,也对早期的斯瓦希里考古工作者产生了深刻影响。
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非洲本土知识精英的成长和斯瓦希里历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此类外部起源的观点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反思。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斯瓦希里历史研究领域内各类学者集体反思的氛围下,考古学者并未落后。这一阶段的考古工作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首先,越来越多的非裔学者加入到考古的队伍中去。不过,早期投入考古工作的非洲学者多经受西方教育,其中的佼佼者多有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知名院校的学术背景,因此其研究方法因袭西方甚多。其次,东非本土的考古机构也纷纷建立,对本国考古学者展开的工作予以支持。只是,在考古工作方法和研究方向上的进展,仍是由外来学者率先打开局面。
毕业于剑桥大学的马克·霍顿1980-1988年对上加遗址的发掘,是新一轮研究取向下最早进行的大规模系统发掘。在上加的正式报告出版之前,马克·霍顿根据上加发掘的阶段性成果,已经就斯瓦希里文明的本土渊源进行了一系列论述。他还根据刚出版不久的曼达报告,重新评估了曼达出土资料提供的证据和线索。在1996年出版的上加遗址考古报告中,马克·霍顿明确反思了前人发掘与研究中的问题:“有利于斯瓦希里人亚洲起源的考古证据,很有可能是发掘方法、调查设计和遗物复原方法的结果。这一问题包括三个方面:发掘集中于有石质建筑遗存的遗址……发掘进行时,石头墙体会被辨认,但木骨泥墙却会因发掘技术而被忽略……遗物的收集比较随意,很少过筛……”这样的批评透露出马克·霍顿对上加遗址发掘的要求。
马克·霍顿在上加多个重点地区布方(Trench,报告中缩写为Tr),但也并未忽视次要区域,在边界地带和疑似遗迹地带均布有探沟(Test Pit,报告中缩写为TP),这样的方法,这样的设计,使得研究者有可能较为全面地了解聚落情况。马克·霍顿对地层的揭露较为细致,他不仅关注石质建筑的变迁,同时也对木质、茅草建筑留下的柱洞予以关注和记录,因此较好地揭示了上加聚落从建造木质建筑到石质建筑的过程。霍顿对遗物的披露非常详尽,不仅包含了之前报告中均会提到的当地陶器、外来陶瓷、玻璃器、钱币、珠子等,还另辟专章,邀请动物考古学者对出土动物遗存进行报告和分析。同时,霍顿也注重利用科技成果,在分期断代时,对多个标本进行了碳十四测年,引为参考。除了更丰富的细节和内容外,上加报告的结构安排,也显露出霍顿求新求变的意图。他将当地陶器分为四期41型,将当地陶器部分放置在遗物中的首位予以报告,这本身意欲表明,虽然当地陶器的时间敏感性不强,但其数量众多,亦有先后时序,能够作为当地文明分期的参考。另一方面,与前人不同,霍顿并未预先告知读者分期成果,而是在完成遗迹遗物的报告后,才利用前文众多材料,将总的分期成果列表并一一分析。这样的安排,更符合研究过程的一般顺序。总体而言,上加的考古工作树立了斯瓦希里地区考古工作的新标准,其方法、技术以及报告方式,都较前人更为细致,虽然在空间分析、植物考古等方面其仍可有进步空间,但至今仍未见有明显超越其水平的考古工作或考古报告问世。
基于上加的发掘,霍顿就斯瓦希里人及其文明的起源提出了新的观点。他认为语言学、历史学以及考古学上的证据都不支持阿拉伯人殖民说。从上加出土遗物的情况来看,上加遗址最早从750年开始有人群居住于此,他们主要使用的器物是当地陶器和比例极低的萨珊-伊斯兰釉陶,且未见伊斯兰性质的建筑和石质建筑。仅从当时物质面貌来看,最初居住于上加的更有可能是非洲本土人群。就上加聚落的形成,霍顿提出了三种模型。而无论在哪种模型中,其最早的居民都是来自非洲大陆。但是这些人群早在8世纪时,就已经开始利用地缘优势,与来自印度洋的穆斯林商人进行贸易,从8世纪末,上加逐渐出现的清真寺建筑和石质建筑来看,在贸易合作的过程中,确实应当不断有人皈依伊斯兰教,正因如此,才会出现上加的星期五清真寺。
上加报告的出版前后,非洲学者查米(Chami)以坦桑尼亚沿海地区考古材料为基础,对公元1000年之前斯瓦希里文明的探索引人注目。与早期学者不同,查米聚焦于本地早期陶器的来源和分类,并对这些陶器进行分期。查米区分出并重新命名了EIW(Early Iron Working,公元纪年-6世纪前)、TIW(Triangular Incised Ware,6-10世纪)、PW(Plain Ware,10-13世纪)、NP(Neck Punctating,13-15世纪)等类型。查米的分类,相对厘清了非洲本土陶器的面貌。霍顿在撰写上加报告和后续研究中,就利用了查米的工作成果,追溯上加居民的来源。查米的工作也促使后续研究者进一步探究斯瓦希里人形成之前东非沿海地区的居住人群情况,及其与红海等地的交流。
霍顿、查米等人的发掘和研究强调了斯瓦希里人的非洲根脉,但是其发掘成果仍然显露出伊斯兰教及其他外来因素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原本对斯瓦希里文明相对简单的解释由此被解构为几个问题:一是最早的斯瓦希里人是如何出现的,即起源问题,由此又引发了人们对于更早历史和人群活动的追溯;二是沿海聚落究竟是如何伊斯兰化的,而伴随伊斯兰化而来的种种物质,如石质建筑,似乎又促成了聚落的质变——即东非沿海的众多聚落城市化的问题。斯瓦希里考古研究的关注重点由此生发出诸多新的分支。起源、本土与外来、伊斯兰化、贸易、建筑等诸多主题逐渐成为斯瓦希里考古研究的热点。
在80年代之后,斯瓦希里地区的考古工作也日益普遍。非洲当地机构在柯克曼、奇蒂克等人研究基础之上,对东非沿海地区进行的较为普遍调查刊布了东非沿海地区的数百处不同规模的斯瓦希里遗址,展现出历史上东非沿海地区的盛况。从肯尼亚北部海岸直到莫桑比克,诸多重要遗址,如马林迪、格迪、蒙巴萨、奔巴、桑给巴尔、基尔瓦、科摩罗、马达加斯加等,几乎均有较为深入的发掘、研究工作,且参与的学者来自世界各地。多学科、跨地域背景学者的参与,使得考古学科中最新的方法、技术和理论在斯瓦希里文明的探索中得以运用,不少学者也将斯瓦希里文明的演变纳入到人类普遍的文明发展模式的框架下予以思考,斯瓦希里文明的考古研究由此进入到更为广阔的视野中。
二、从中国出发——斯瓦希里考古中的中国陶瓷
在斯瓦希里考古诞生之初,中国学者就开始了对东非沿海地区成果的关注。这一关注除了有特定的中非友好的背景外,也是因为东非沿海地区出土了大量中国陶瓷。夏鼐于20世纪60年代初先后撰文两篇,介绍东非沿海出土的中国陶瓷和其研究意义。此后至80年代,马文宽、孟凡人根据当时刊布的一些外文资料,撰成《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一书。囿于材料限制,此书的图片资料相对简陋,但却为国内关注中国陶瓷在非洲的流布提供了重要线索。随着我国国力不断提升、考古学科的长足发展,我国研究者的研究对象日益外延,赴外考古的条件相对成熟,因此2010-2013年,北京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与肯尼亚国立博物馆联合对东非沿海地区进行海、陆发掘,取得了丰硕成果。这项考古工作是我国首次赴非发掘,虽然最初项目的启动以郑和研究为契机,以中国陶瓷为主要对象,但是在实地调查、发掘和研究的过程中,国际学界众多斯瓦希里研究的成果引起了项目参与者的重视。因此,在完成项目任务的基础之上,我国学者试图充分吸收海外学者的已有成果,并利用自己的优势参与到斯瓦希里考古的研究之中。近年来,秦大树团队在东非沿海出土的中国陶瓷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除重新整理披露资料外,在两个主要的研究方向上有较好推进,一是厘清中国陶瓷输入东非的阶段性;二是探索了斯瓦希里社会中中国陶瓷的角色。

图 7 当地柱墓上镶嵌的中国陶瓷
无论斯瓦希里文明起源议题如何走向,但学界基本公认,外来文明因素和国际商贸活动是斯瓦希里文明的重要特色。而中国商品在其中曾占有一席之地。以中国为基点,探索海上丝绸之路和印度洋贸易的实际影响,我们有必要了解商品流通路线和消费市场的实际情况;而换位思考,以东非沿海为基点,观察非洲大陆商圈与海外商圈的齿轮耦合、商品交换,有利于我们清楚认识海上丝路的实际作用与中国商品的地位。另一方面,斯瓦希里文明是具有特色的人类文明模式,斯瓦希里考古是世界考古学的一部分。对它的探索,亦是我们通过观察他者、观察世界,进而反观、反思自身文明的一部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思索自身的文明模式和人类的普遍行为模式。正因如此,我国学者参与斯瓦希里文明诸多议题的探讨颇有必要。
欧美学者和非洲本土学者对斯瓦希里地区的多年考古研究,成果丰厚。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海外考古的方法、技术、理论多有吸收,能够较好地解读此前斯瓦希里考古的研究成果。这也意味着我国学者的介入实际已经站在了一个较高的起点。在这一起点上,我国学者的开拓优势或在于,虽然欧美学者亦重视东非沿海地区发现的中国商品遗物的分期作用和全球史意义,但中国学界多年来就本国商品循环过程的诸多环节,特别是生产环节已经积累相当多的比对材料和相应研究成果,有利于在这一方面展开更详尽的研究;另一方面,欧美地区、中东地区在古代和近现代,均曾深入参与过东非沿海的“殖民过程”和文化交融过程,这使得欧美学者、中东学者乃至非洲本土学者,均有“利益相关者”的背景。中国虽有商品进入东非沿海地区,但在历史上从未与东非沿海有过大规模冲突或殖民关系。正因如此,中国学者有可能站在更为客观的视角,对这一地区文明的形成和演变予以审视。
惠勒爵士曾说,东非的历史是由中国青瓷写成的。这一观点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中国学人对斯瓦希里文明的探索负有责任。如今,国家和学科的发展已经赋予了当今学人“开眼看世界”的机遇和挑战,而如何在实践中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正是我辈应当思索的。
本文已经丁雨老师审核
文稿丨胡好玥
摄影丨胡好玥
编辑丨龚梓桑
审核丨沈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