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陈星灿,英国国家艺术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教授杰西卡·罗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先后进行第二届“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旨报告,报告由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沈睿文主持。
圣水牛和中国家养水牛的起源
陈星灿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圣水牛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自1928年的殷墟发掘以来,圣水牛就被认为是本土起源的家养水牛,与水稻农业的发展密不可分。在殷墟发掘后,德日进和杨钟健就将圣水牛列为家畜,并认为其是本地起源。李济先生在1957年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中也明确提出圣水牛是家养水牛,并认为商人已驯养水牛用于农耕。然而,这一观点缺乏充分的考古实证。
直到21世纪初,我和刘莉教授及杨东亚教授共同开展了一项研究,我们在全国各地出土圣水牛的遗址和地点采集了大量样品,对这些圣水牛样品的骨骼形态进行了观察与测量,并对康家遗址的圣水牛样品进行了DNA检测分析。从中我们发现,虽然许多中国动物学家相信家养水牛是在中国本上驯化的,并与目前已知生活于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圣水牛有关,但圣水牛出土骨骼样品分析却并未显示出驯化特征。具体而言,从种属特征来看,更新世时期的短角水牛和全新世时期的圣水牛在形态特征上更为接近,两者相对于大多数其他种的更新世水牛而言体量均较小,我们据此推测,全新世的圣水牛可能是从短角水牛演化而来。从区域分布来看,在更新世时期,圣水牛出土的遗址和地点基本上在全国范围内、从东北地区到西南地区都有分布,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分布的面积更广,向北一直到长城地带都有相关发现,但到了青铜时代早期,圣水牛出土的遗址和地点基本上集中分布在黄河和长江流域。从体质特征来看,圣水牛的头骨和肢骨测量数据与王氏水牛、杨氏水牛以及现代的家养水牛都有较大差异,并且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圣水牛的体质特征都没有显著变化,并且并未出现因驯化而变小的情况;从屠宰模式来看,圣水牛基本在成年之前就被屠杀了,从而综合反映出其野生的特征。
康家遗址圣水牛样品的DNA分析则进一步显示,圣水牛与现代家养水牛没有直接关系,家养水牛可能是从南亚传入中国的。之所以我们得出这一结论,首先是因为南亚和印度河谷发现的最早的家养水牛遗存在哈拉潘文明的哈拉微拉城市遗址得以确认,这一遗址的年代被定为公元前三千纪之末,驯化的时间也许还要早在哈拉潘文明之前,但具体的驯化过程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在中国西南地区,已报道的最早的家养水牛证据来自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同时,进一步的证据表明,中国的西南地区与南亚地区存在长期的文化交流,战国时期的滇国就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两个地区已经建立了联系,而这一联系的开始时间可能还可以继续往前推。由此,我们可以拟定家养水牛从南亚次大陆向东传播、然后经过云南传入内地的这一假说。
此外,考古学和图像学的证据也都支持圣水牛是野生的,且与现代家养水牛没有直接传承关系。考古上水牛的形象最早出现是在早商时期的郑州地区和城固地区,这是两个发现圣水牛形象最多的地区,而且后来成为饕餮纹的主要形象来源。西周时期,虽然圣水牛骨骼出土的数量减少,但其形象仍然广泛分布在青铜器和玉器中,直到战国晚期,这类形象逐渐减少,曾侯乙墓中发掘出土的铜鼎上的圣水牛形象是迄今为止最晚的考古记录。法国的古文字学家雷焕章先生论证了甲骨文中的“兕”形象就是水牛,甲骨文卜辞中记载的商代猎捕“兕”的活动也表明圣水牛是野生动物。由此可以推断,商周时期的圣水牛是野生动物,而非家养。
综上所述,目前已有的证据表明,圣水牛是野生动物,中国的家养水牛并非来自圣水牛,而很可能是从南亚引入的。但具体传播路线仍存在比较多的证据缺环。例如,我们尚不清楚水牛是如何从南亚传播到东南亚,并最终到达中国南方的。此外,关于水牛与犁耕、水田之间建立关系的时间也晚于圣水牛骨骼在考古发掘中的消失时间,中间存在大约1000年的空缺。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基于西周到东汉时期的水牛骨骼证据,探索家养水牛的起源和传播路线。

陈星灿进行主旨报告
1890—1980 年代西方的古代中国研究
罗森 Jessica Rawson
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教授
自16世纪起,中国的丝绸、漆器、瓷器和茶叶通过贸易出口到欧洲并广泛流行,但这些工艺品却未能传达出中国早期文明的形象,尤其是古代的青铜器和玉器几乎无人知晓。
陈梦家、李学勤及日本学者所编写的目录已经对美国或日本收藏的中国青铜器有所介绍,而伦敦和瑞典的学者和收藏家则在研究和理解古代中国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基于古代中国青铜器藏品的学术研究。
伦敦的首批古代中国文物收藏始于19世纪末,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伦敦收藏家是乔治·尤摩弗帕勒斯(George Eumartapaulos,1863—1939)。目前,这些伦敦收藏家的许多青铜器藏品都收藏于大英博物馆。收藏潮流在1935—1936年皇家艺术学院举办盛大展览时达到顶峰。自二战至1960年代的艰难时期,这场展览成为欧洲理解古代中国的重要里程碑。
瑞典是当时欧洲、甚至可能是西方研究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学术中心。约翰·冈纳·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较早在中国开展了考古发掘与研究,而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Gustav Adolf VI)则热衷于支持中国的考古工作,并推动古文献研究和安阳周边的古物收藏。高本汉(Berhard Karlaren,1889—1960)遵循蒙特留斯的类型学方法研究中国的青铜器。卡尔贝克(Orvar Karlbeck,1879—1967)则曾在安阳附近开展过三次收藏之旅。李济在1927—1938年对安阳进行了发掘,这一发掘也刺激了瑞典学者们对于古代中国的兴趣。这一时期上述关于古代中国的收藏目前都保存在斯德哥尔摩的瑞典东亚古物博物馆。
在古代中国的青铜器中,青铜武器尤为吸引包括我在内的欧洲学者。这主要源于欧洲人对欧亚草原有关的文物的广泛兴趣,而与中国类似的青铜武器也在欧洲东部交界的欧亚草原西部制作与使用。欧洲对古代中国青铜武器的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三代。首先,在1890—199年间,一些青铜武器的藏品目录得以出版,很多西方学者深受藏品目录的启发,大英博物馆也收藏了一些相关物品。第二代学者则以大英博物馆前策展人罗越(Max Loehr)与沃森(William Watson)为代表,他们的材料来自博物馆收藏与考古发掘,他们都认识到了短刀的重要性,但仍未意识到短刀与匕首之间的重要区别。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三代学者重新审视了中国的青铜武器与外部文化之间的联系,这时期的代表人物如罗越的学生胡博(Fitzgerald-Huber)和维吉尼亚·凯恩(Virginia Kane)、俄罗斯学者康斯坦工·丘贡诺夫(Konstantin Chugunar)、北京大学的曹大志教授、哈佛大学的张光直教授与他的学生罗泰教授(Lothar von Falken-hausen)、北京科技大学的梅建军教授。他们研究发现,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武器有独特的本土铸造技术,这一技术保护了中国不受边境侵扰,早期冶金技术也随着人群及其牲畜一同跨越了欧亚大陆。
上述学术史的阐述得以证明,对研究古代中国而言,西亚、伊朗之间的对比研究十分重要,也进一步显示中国在世界文明版图中的重要性。研究古代中国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现代中国,从而打开交流的通道。

罗森进行主旨报告
两个世界的徘徊——中国历史时期墓葬的演变
齐东方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丧葬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一项普遍现象,在不同文化中展现出丰富多样的形式与内涵。中国的丧葬文化尤为独特和复杂,既体现了中国人对生死的深刻理解,也反映了社会伦理、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的交织影响。
本研究源于1996年到1998年我和同仁所做的“中古时代丧葬研究”的项目,并集结出版了《两个世界的徘徊:中古时期丧葬观念风俗与礼仪制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由此出发我认为,生死观是推动墓葬研究继续深入的重要切口,它不仅仅反映了中国古代人们对生死的深刻认知与回应,还影响了丧葬的礼仪、形式,甚至推动制度的演进。在对中古丧葬的研究中,比较研究方法是一个重要的手段,一方面我通过横向比较,探讨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在处理死亡问题上的差异;另一方面则通过纵向比较,追溯中国古代丧葬文化的阶段性变化,以理解其背后的文化逻辑与社会动因。
从横向比较的视角而言,中国人的死亡观念复杂且层次分明。中国传统文化对死亡的称谓多带有隐晦和定性的特点,并在丧葬实践中通过一整套等级化的丧葬制度与风俗来处理应对这一问题。从等级、年龄和死亡方式等维度,中国社会对丧葬进行了严格的阶序化区分。这种体系在世界范围内显得尤其具有系统性和延续性,这也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伦理与家庭观念中的孝道思想。中国的丧葬文化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事死如事生”影响下的厚葬行为,这种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孝道文化,并与“等级”观念紧密相连。而让死者得到隆重的丧葬仪式不仅是孝道的体现,也是子孙后代赢得社会尊重的重要方式,这说明丧葬不单是亲情的延续,有时更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反映。二是土葬的长期普遍性,这种埋葬方式自古代起就深受重视,延续至今。
从纵向比较的视角而言,中国中古时期墓葬制度经历了三次重要的转折。西汉中期是第一次转折,礼崩乐坏之后,逐渐形成了汉制。从西汉中期开始,“室墓”逐渐取代了椁墓,标志着墓葬形式的重大变革。晋制的建立则是第二次转折。东汉末年的持续战争导致盗墓活动猖獗,人们开始对厚葬产生疑虑,怀疑墓葬是否能够真正成为死者安息之地。几代统治者的一贯坚持,加之普通人也认识到“厚葬无益于死者也”,最终迎来了新的墓葬变革,丧葬活动开始在新的系统下运转。“安史之乱”后是第三次转折,随着原有秩序的打破,乞求安宁、消灾解难成为人们普遍的向往,“招魂葬”从民间习俗上升为正式的国家礼制,同时过去繁复的礼仪形式也逐渐不为人们重视。
结合上述的横、纵向视角的阐述,我们可以发现,正是生死观变化所引起的对原有的礼仪制度的怀疑、挑战,从而在社会中掀起了“移风易俗”之风,使丧葬礼仪制度做出种种退让或修改。因而生死观的变化不仅反映了人们的心理变迁,还揭示了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转型。尽管考古发现的墓葬是碎片化的实物史料,但经过连缀、拼合,可以大致展示出演变模式,将抽象的生死观鲜活地展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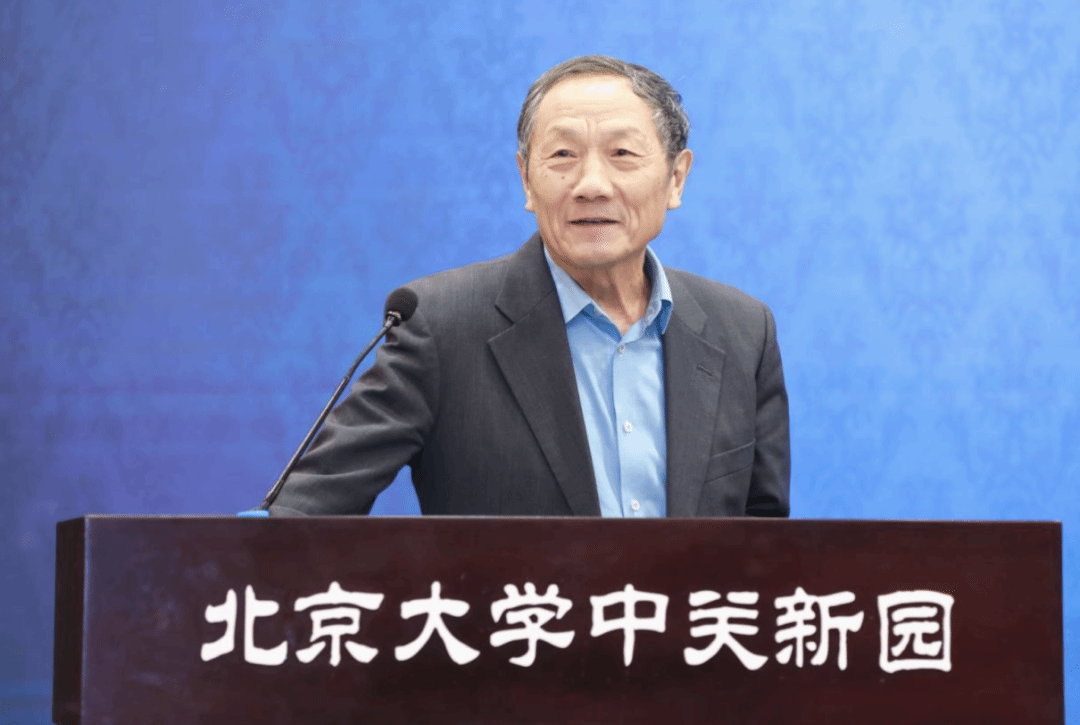
齐东方进行主旨报告




主旨报告现场